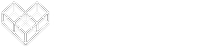正文 【耽美】瓊花落(完) — 瓊花落
小僧清修多年,本来习於平静,奈何这小书生忽然闯入,扰得我不能安宁。
话说从头,一日我在草堂里打坐,心思几欲神游,忽然间,外头木门「砰」的一声打开,吓得我连人带屁股飞了起来。
蓦地回头,只见门边倚着一位好漂亮的相公,皮白肉嫩,五官精致,一对眼睛眨巴眨巴很是水灵,就是稍嫌秀气了点,不似观音皇子,却似祂後边侍奉的龙女。
他一身粗布青衫,就连缠头的包巾也是青色的,许是不习於向外人搭话,他懦懦的说:「大师,请问探春湖该往何处行?」
当时我没听清楚,以为他问往哪儿探春才好,我说:「书生哥,不是小僧要亏你,九月分明是入秋时节,你往哪里探春去?」
书生懵了懵,像是不知从何回话好,一会儿方说:「大师,莫调笑我,我向您打听探春湖的位置呢,求您大发佛心,指点小生。」
这回我可听清楚了,道:「探春湖在隔壁那座山头上,想你是摸错路头,或鬼蒙了眼,才走这瞎路。」
书生一听我这话,脸都鼓了,可是还必须求问於我,不好发作,只得闷着头,不发一语。我正欲劝他宽心,说:「公子别急着走,可在青灯边稍事歇息,我替你准备烤火暖身,你也顺便听我讲几卷经文。」可惜他头也不回的走了,叫我好生难料。
我在草堂里继续打坐一会儿,听这窗外的风雨声沙沙作响。不一会儿,书生哥又回来了,他靠在门边,抓着外套簌簌发抖,老旧的木门合不拢,歪在外边嗄嗄作响。我看他这小模样,俨然孔夫子被追杀之时,颓然如丧家之犬。书生哥连一声招呼都不及说,忙带了门,跑进屋里躲雨。「兀的突然,下个大雷雨,把我也吓煞了。」
我说:「敢问这位公子,因何来此荒凉之地?」书生哥向我合袖行礼,我双手合十回之,看他如此讲礼,铁定是个儒生。书生哥说:「大师晓得,我欲往探春湖边的捻梅庵行,本想求取经书宝藏,不料这番走岔,才误闯贵宝地,请问此为何处?」
我答道:「确实差远了,此地是秋湖畔,说起湖边这破庙,虽是古煞,但毕竟参拜信众少,来参禅的也不曾,自没个名号。」
书生哥闻言一喜,「若是大师愿意,小的愿取一名号,请大师参酌。」
「请。」
书生哥说:「吾见寺外枫树两排,枫红满地,虽说此名甚俗,不入雅士之耳,然观其名,取其义为『红叶寺』,岂不与『秋湖』相配?」
妙哉,妙哉,难得小书生出此语!「如此正好,虽是俗名,也需慧眼辨识,更需慧心想出,小僧这去备墨宝,烦先生挥毫落款。」
「有劳大师你了。」
大字一落,笔走龙蛇,我在旁捧砚,那人捉袖写字,刷刷几笔,浑然天成。我挂在墙上,约定待放晴时分,再出去以木刀临摹,以分解本庙是「红叶寺」,莫再使过路行人混淆作捻梅庵。
一盏茶时分过去,山中暴雨未曾停歇,扑簌簌的雨点子已好些打进窗内,濡湿地板,我吩咐他挪动蒲团,便他避远。那书生哥刚才还一派嶔崎磊落,叫他挪近些,他反而不依了。我说:「也不是个孤男寡女,从何怕得如此?」
书生哥赧然一笑,搔着头说:「实不相瞒,我看街谈巷语流行的那些小说,里头总爱叙述山庙的和尚,从喝酒吃肉到调戏妇女无一不少,只怕,只怕……」
「只怕什麽,就你那皮相,也想劳烦小僧对你龙阳。」
「嘿。」书生哥或许以前真有这困扰,恰巧被我挑中心事,又怕处处避讳,反显得他阳刚气不足,当真挪近了点。
我看外头天色已晚,今日定是出不去了。书生哥也问到:「大师,就你看这山雨,何时能停呢?」我说:「这霪雨一大,非但不停,连石头都给砸崩下来,有时镇外就来人把路给封了,於是上山的人便越来越少,自我师父死了以後,师兄师弟都走了。」
「怪不得,人说和尚冷冷清清,只有你怪热情的,处处跟人打趣。」
那书生听完,眉头一垮,一时也消了下山的打算,跟我闲聊起来。「是了,怎麽你师兄师弟都下山去,就你一个还在这儿顾庙?」
我笑道:「可不是为了遇见你,替你指路?」
「呃…你…」
「唉,别气,瞧你脸皮子这麽薄,说点逗趣话儿,脸就红得能出水。就你一个小书生,哪来那麽大的份量驱使我?」
书生听了我这话,铁定也晓得自己太过小性子,苦笑着在那儿尴尬。
我说:「庙里毕竟有佛像,大家都走了,谁来薰香供奉呢?下山去也不能当散人,我不如待在山上成日清闲,也多亏佛祖保佑,否则住在这麽高的山上,难保哪天被雷打死。」
书生听笑了。「被雷打死就免了。师父的话让人好生向往,小生也想过这般闲云野鹤的生活。」
「你以为梅妻鹤子、闲云野鹤,我看是挑水送柴,处处忙碌。」
我略拍拍他的肩膀,那书生抬眼看我,看得我忽然一慑,有些怪异。我问:「你为何要往隔壁山上求取经书?」
「大师避世甚久,有所不知。」书生正襟危坐,换了个语气,正色道:「这年头战乱正炽,好些书卷都被劫掠殆尽,只有寺庙未曾遭到波及。乱世中,有哪边适合读书?我就图个清净去处,最好有书念,於我赴京赶考有助。」
我一听,这不正是我们寺麽?「小僧这破庙,连只老鼠都不屑光顾,何况战中武夫?论起吃斋的、念佛的、供膳的、洒扫的,从上到下就我一人,只要我不去扰你,那也是十分的清闲不说。除此之外,别的好处一一没有,只剩经书不少,自先秦以来,许多前朝的资料都供在这里了。」
书生听完,面有喜色,很是意外。我见时间不早了,道:「公子饿麽,我去备点素菜素饭与你。」
书生摇头,「饿是不饿,就是身子好乏了,明日想早起看书,敢问寺内有无空的厢房,可供小生暂宿?」
我道:「除了小僧平日作息的禅房以外,其余的日久无用,都积了好厚一层灰,我这就去替你整理一间出来。」书生一听,忙说:「怎麽好劳烦你?不过一宿,暂借你禅修之地即是,还请大师多担待。」
「不劳烦的,请。」
当晚,同床共被,聊了许多闲事,我向他讲佛,讲山,讲动物、他向我讲外头世界,讲战乱,讲读书,我诱他入山门,他请我出山门,我们俩虽说不大相似,又有些说不出的相似,暧昧难明。
一转眼,四年过去,小书生已将我佛寺里的书大致参阅一遍。
我见时候已到,问他:「书生哥儿,你这就去赴考吗?」
那书生哥气焰甚高,志气分明,笑嘻嘻回道:「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,两样皆成,我可赴考矣。」被我一问,他随即款理行囊,不亦乐乎。
我晓得,老年人般荷锄归隐的生活,对前途光明的小夥子而言有如囹圄。桃溪不作从容住,秋藕绝来无续处。这样好的一座名山,如斯美丽的春光春景,只要他想,甘甜的山泉与鲜美的山菜时时为他预备,他却硬是要脱离世外桃源,只为一头紮进那被我弃绝的尘世。
我没劝他,因我知无从劝起。看他兴致勃勃,我怕他栽得一头空,叫他以平常心面对一切如是。他说:「怎使得?这四载以来我饱读经书,那些策论、上书难不倒我。」我想,世间的险恶正是於此,岂是你有才学就真得重用?若真如此,外头又怎有众多失意之士往燕赵一带隐匿?
我吩咐他走好,慢慢行,勿操之过急。他走的那一天,很早就起床,把我给惊动了。说不上是什麽心情,我一边装睡,一边偷偷地看他穿脱衣服,观望着他赤裸而纤瘦的背,还有一身白皙的皮肉,直到他最後穿戴整齐,提着行囊离开房间,我都未曾起床送他。
四载光阴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我和他算个同窗,更算个同床。俗云:「十年修得同船度,百年修得共枕眠。」我与他的缘法说来不浅。
那书生好是好,可他一走,与我那些去了的师兄弟们有何异?我那仙去的师父,还有下山的师兄弟们,於今在何处?
人生不见,动如参商,许多人一生未再相见的时间,比起相见的岁月多太多了。既然一生只此一回能相遇,不如相忘於江湖!
※
一日,我坐在庙门外,正在喂一头鹿吃草,却闻远方传来踏歌声,唱着「归兮,归兮」,那声音嘹亮,把幼鹿吓跑了。我手上掬着一把草,不知做何用,索性扔在地上。
那踏歌声逐渐接近。我自草地上站起来,抬眼一望,欸,不正是前两年那小书生麽,怎麽回来了。
那书生一袭粗麻衣,爽朗的向我打招呼:「大师,我回来了!」除了眉眼依旧分明,他的气质显然与先前并不相似。不知怎地,一见了他,竟蓦地想起他那白皙细瘦的背影,我尽量忽略尴尬,拍拍他的肩膀,笑着答他:「小崽子怎麽回来了?不是嫌弃这好山好水太过无趣,想到天涯里四处闯闯麽?」
他搓搓鼻子,也笑答道:「年轻时容易心热,血性子时常跑上来,总想着要建功立业;随着马齿徒长,饱尝骚人迁客之苦,才渐渐的察觉此非我所欲也。」
「是了,瞧你说的,彷佛两年间你已历尽一世的沧桑。」
「我确实历尽了一世沧桑,你都不知我想找你,找得多苦!」
「喔?」这我倒很好奇了,「我不一直都在这儿待着?跟我等了两年一比,你到底苦在哪里?」
「以前未曾把上山的路记下,於是我四处寻访,竟未曾问得有谁知晓秋湖在何处。好一个隐匿的世外桃源,与人世几乎断绝了关连!」
我聚精会神地听,听他是怎麽千里迢迢的过来,不论是为了我、为了这山、还是为了这破庙。他说:「我想『呦,这不是武陵人的情节吗?』虽在山上休养四年,不过出去两年,我倒成了风尘人,被桃源抵挡在外。当年毕竟是我舍桃源,并非桃源舍我,於斯地步,我倒谁也不怨了。」
「前会子,我一不注意晃了进来,当时只知迷路,十分怨叹。就在我灰心丧志之际,蓦然间豁然开朗,林豁溪涧都清晰起来了,这不正是我与你一道见过的日光吗?我知走对路子,再朔溪而上,来到山顶,便见着大师你与秋湖了。」
「这是顿悟啊,」我道:「佛祖有意指点,这是予你的契机,着你在红叶寺里修行,作个佛门弟子。」那书生闻言,两眼放光如星,立刻上前执住我的手,「大师、不,师兄,有劳你了!我在此与你作个同门可好?这回,终於不再是你读你的,我读我的,我们可以一起修读佛法。」
「看来你真是有意思要跟我过上一段日子。」我搂着他的肩膀,拍拍他的手臂,「当然好,小师弟,我与你真是佛缘不浅!」
那书生眯着笑眼,高兴的说:「我道行尚浅,尚不能解何为『色即是空』,所以我还有许多难解难舍的事物,不论如何,我定不像你过去那些同门,把师兄你抛在脑後。」
※
「--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尽誓愿断,法门无量誓愿学,佛道无上誓愿成。」
带着那小书生读完四弘誓愿,我缓缓动刀,替他落发,看他满头的青丝逐一飘零在地,成了没有意义之物,虽说落尽三千烦恼丝,我却觉今儿才是真烦恼的开始。
替他烫上戒疤以前,我忍不住摸摸他光滑的头顶。他跪在佛像前,眼神飘忽,神色恍然。我问他:「只要烫上戒疤,就不可再反悔了,你真的愿意吗?」
「师兄,别多说了,我意已决。」
他在踌躇,而我替他感慨。将点燃的香角炙在他的头上,随着第一个戒疤烫好,我自蒲团上扶他起身,说了句:「毕竟最初是我邀约你的,现在才说是有些过分了,但我现在觉得你其实不适合遁入空门。」
我和小师弟过了两年舒心日子,每天早起去挑水,轮流做膳食,吃饱就操课,有时我向他说经文,他一有心得便向我阐发,我们看的是同一本书,说的是同一题目,比起以往孤独的日子,如今我们很能互相激发,每天聊的都是佛法,心里想的也是佛,双方都很喜欢如此作彼此的良师益友。在山上不乏食,也不畏冷,一人两套破袈裟已够用,夏天我用戒刀把小师弟的长袖长摆割去,冬天时若要替洗就接回去。
他初入门时,我带他到山上辨认山菜,他看满山遍野绿油油的,没一样认得,我亏他:「真不愧是儒生,上山三两步气喘如牛,太阳晒一会汗如雨下,见了山菜没一样知,当真是四体不勤,五榖不分。养活自己尚且成问题,如何能道济天下人?无怪乎一入世便败兴而归。」小师弟脾气很好,半句也没回嘴,可自那时开始,他就默默的把全山上出了哪几种山菜全记下来。
某日,庙里的针线与盐醋没了,我背些乾柴下山换购,店里的老板娘一见我,劈头就说:「国里正在流行瘟疫,小师父得小心啊。我看你们是修行人,佛祖铁定会保佑的。」
我想道,我们这些修行人,难道是为了求佛祖的保佑才修行?
修行人求保佑,世俗人更要求保佑,但日日夜夜过去,总是有固定的人们生生死死。佛祖若保佑修行人,就是偏心,有私;保佑了世俗人,却是不厚道,愧对佛门子弟。想来,佛祖最终定是谁也不佑。
谈到生死之际,总是很难将所有缘故都归罪给神佛,死於非命也罢,正命也罢,个人的因果造化总是占其泰半。
那老板娘还抱着一个孩子呢,希望她们不会受到瘟疫的波及。晚间,我走在石板道上,抬眼见晚霞如血,苍凉的阔空有大雁孤飞,日暮时分的山风兀自寒冷,我虽全身发寒,脚步却不禁推迟,不愿归去。我忆起自己也曾是那麽小的孩子,在襁褓里让母亲抱着,待到长大了些,母亲就牵我的手出去散步……如今,浪费十数年光阴,我是个真正的大人,既未陪伴、孝顺过父母,也从未贡献社会,这世上有无我都罢,竟是一点改变都不曾。
我悟到自己的想法当下完全偏离了沙门。当晚,我和师弟依旧同榻而眠,窗外正在夜雨,很不平静,雨声淅淅沥沥,风声瑟瑟萧萧。我夜不成寐,翻了个身,发现师弟也在翕动。我拍拍他的手臂,他翻过身来看着我,「师兄,你睡不着吗?」
黑暗里看他那双晶亮的眼睛,哪里像是睡得着。「睡不着。」我细声道:「自我遁入空门後,这是我少数无法入眠的夜晚。」
师弟把双眼眯得弯弯的,笑道:「佛家最是清净,与尘世诸繁杂绝。心轻万事如鸿毛,有营何止事如毛。活得清心,自然不曾难睡。」
我看了一会儿,不禁伸过手去摸摸他滑嫩的脸庞。他把手盖在我的手背上,我颤了会儿,叹息道:「师弟说得对,是我心生杂念,日後恐怕再没资格,让你称我为师兄。」
「何意?」
「『也无风雨也无晴』是宋代大儒苏东坡所云,他与佛祖同是历尽苦难,受尽沧桑,才点破天机,得以证道。这辈子我却未曾出世,反先避世,与所谓『避人之士』有何异?」
「再年轻的时候,我也什麽都不管,却不是因我悟了道,而是因我狂狷。如今,我快老了啊,不想抱憾而去。今夕复何夕,今夕何其多?我最怕哪天,忽然就没了明日。」
师弟静静听了一会儿,眨眨眼,看似有了困意,直到我话声落下,方道:「死即是生,生即是苦,你竟贪恋着生,这是你的造化啊。师兄,这一去,你还回来麽?」
「或许去个一年半载,我也将同你一般索然而归,因这空门的日子太舒坦了,岂是凡俗可比?」
「虽云如此,那汲汲营营的凡俗,仍是在召唤师兄你前去。」
师弟深深吐了口气,像是十分疲累,他语重心长的说:「老话一句,『人无信而不立』,师兄请千万记住自己所言,莫在外头迷失了。」
※
离别一何久,七度过中秋。这一去,竟是七个年头不见,回望我对师弟信誓旦旦的约定,倒显得我乐不思蜀了。尘世啊,尘世,这污浊之世,当真值得我抛却师弟、抛却红叶寺,继续留恋下去吗?
可爱的小师弟若是个聪明人,就不该记得那约定,也不该继续等我。一个转念,我又想,他就算继续留在红叶寺里修行,也非是为了我,而是因他自身悟道有成,既是如此,又与我有何关连?
升官发财後,烦恼的事甚多。我过惯清闲的日子,乾脆什麽都不管,为此,妻子每天都会责骂我。会与她继续生活,一来是她替我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,二来则是不管她爱怎麽骂,我都能忽视她。
有时,我总忍不住的想,还是与师弟一起的日子惬意,每天晚上,他总是静静的躺在我的卧榻边,一个字都不曾多说,哪怕撞着他,摸着他,他也不曾把他醒来,不知是刻意忍着,还是真睡得人事不知。
随着日月流逝,头发不知觉间变长了,我刻意拨了些浏海来掩饰戒疤。这戒疤总在提醒我,人间非是我之归属,山上才是我的家园,但是与我有血缘的家人如今都在京里啊。是我亲手背弃了五戒,也如同我师弟所云,背弃了「桃花源」,既然如此,我又哪来的脸回去。
在京城,我有房有马,有妻有子,每晚就寝时,当我拉起床帐,却觉着彷佛少了什麽。明明头下垫的是玉枕,盖的是合欢被,衣衾上还绣着花,比起山里的粗糙简朴,比起师弟给我缝的破烂补丁,竟然有种说不出的违和,好像这生活本不该属於我。
一回,妻子坐在客厅绣花,我一踏进门槛便说:「你这女红手艺是该传授。」她停罢针线,抬头一问:「夫君,你说传给谁呀?」我猛然想起,是了,师弟在山上,妻子往哪里给他教习?
自我离开已有七年,不知他的戒刀用得熟不熟悉,针线缝补的手艺有没有变好,自行调理的膳食是否曾毒坏了肚子?想想,这些都是执、都是念,我这个粗鄙的俗人,岂能抱着一车俗念,回到佛门清净之地?自是不该,不得。
当天夜里,吃罢元宵,我正在露台吹风赏月,妻子推开窗牖,向我欸了几声。我回头问她何事,她道:「相国寺请了一位师父讲习佛法,说是不远千里,自山林野岭而来,人们瞧他有清气、有才调,与一般僧人特别不同。我们许久未曾听讲了,不如去瞻仰下大师风采。」
刚喝过小酒,浑身发热,我拿把蒲扇搧了搧,道:「佛法你也听得多了,尝言『一性圆通一切性,一法遍含一切法。一月普现一切水,一切水月一切摄。』佛说的法门有八万四千种,就是耗尽一生也听不完全部,这些个事儿,讲佛缘、顿悟,假若有天忽然懂了,又何须听再多的法?」
妻子十分好辩,忙争着说:「听了也许不懂,没听就什麽都不会懂啊,没听过『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吗?』这都是工夫啊。」妻子要与我辩论,我本是欢喜的,可惜双方路数不同,无法公平讨论,兀的还讲到工夫论上头。
妻子又说:「什麽『一切水月一切摄』?我还千江有水千江月呢。夫君,你不懂,我太久没布施了,心里总有些不安,去听说法还在其次,重点是去向寺庙布施,积阴德!」
我想,就你这神神鬼鬼的性子,能证道才怪呢!可她不是个明白性子,不好向她说明白话,我只好把话闷在肚子里。回思我与师弟初见那时,把他亏得可凶了,他却是一句不骂,也不记恨,就他这点温顺性子,也比我家婆娘好太多了。
我本是个出家人,不强求妇人替我生娃,如今已有了娃,再归入山林里,只要能有个人作伴,像师弟那样的就挺好。
我陪妻子先到镇子上的夜市逛了一圈,替娃儿买了几个灯,回头再抱着娃儿,跟婆娘往相国寺里听佛法。也没想慕名而来者无数,快把槛子踏破了。我听前边儿围观的姑娘们猛往人群里挤,说:「这大师生得很是俊俏,怎的落入空门?」「许是官场失意,你没听说过,这每年呀,有好多没考中的,都抛家弃子,上山隐居呢!」
瞧我听的,原来这些人都贪图出家人的美色,才来佯装听讲,怎麽好呢?我可未曾被这麽称赞过呀!我费尽力气,挤入最前排,终於见到台上那佛友,竟然是我师弟。
师弟端坐在蒲团上,手捻一香珠串,一身猩红色的袈裟。他皮肤甚白,眉目清秀,五官精细,一袭红袈裟笼在他身上,不知是否我心性吊诡,在我看来,竟有些冶艳,尚,不保台下人们也看得心性浮躁,佛性淡薄。
以他修行的岁数,头上不该只有一个戒疤,但因他唯一的师兄离开了,他额上就只会有那唯一一个香疤。我毁伤他发肤就算了,那印子还一辈子都不会消失,而我丢下他不管,算是造业。
案上馨香已备,师弟轻啜一口茗茶,抬头准备讲习,一抬眼,目光倏然与我对上。交会间,我只觉心中平平静静,杳无纷扰,相较之下师弟却瞠目结舌。此时我能放下,便无甚是不能放下的了,而他不能放下的甚多,显是他修行还不到家。
夜里,我先叫马车带妻小回去,自己则夜访相国寺。我叫住一个在外头扫落叶的小沙弥:「烦你为我通知下你们师父。」小沙弥进去通报一声,随後着我进入。案前蒲团与清茶已备,室内香烟缭绕,静坐在案後的师弟与我印象中又有极大的不同,是了,已经七年过去,人怎能不改变?
他一手紧捻佛珠,一手比了个请的手势,一时并不抬头看我,只温吞道:「师兄,好久不见,甚是思念,请坐,请用茶。」说话多有疏离,模样很是生涩,一别七年,虽我仍牵挂於他,他却不免与我成了陌生人。
我在蒲团上坐下,与他打过照面,我双手合十,他亦同样,彼此闭目点了头,我们各自道:「阿弥陀佛。」我没问他为何不离开红叶寺,他也没问我何以不归,兴许是问题没有答案,亦不需答案,最重要的岁月早已荏苒而去,失去的珍贵事物太多,余下的相形一比,只显得飘渺虚无。
茶香与焚香的清烟在室内缭绕,茶香味极为熟悉,是他亲手泡的碧螺春。
一方清冷的月光自窗棂入照室内,觑得师弟苍白的脸更加憔悴,良久,他轻叹一口气,游丝般的说:「原以为师兄在神京无忧无虑,於是我了无牵挂;不想师兄尚未不惑之年,却是白鬓添生,看得我不胜惆怅。虽一人在山上,一人在山下,到头来,又有何差别可说?」此番说来,反而他在山上,也过得并不舒心,这又是何故呢?
我鲜少照镜子,倒不晓得自己早生华发,更稀奇真有这麽明显,让他一眼就看见了?我招手让他过来,「师弟,帮我把白头发拔掉,若是不拔,可是会长得更多。」
师弟淡然一笑,意味有些凄凉,眼神也清清冷冷的,他双手合十道:「阿弥陀佛,白发多或少又有何妨?为了此等小事萦心,是你执着了。」
我亦双手合十道:「阿弥陀佛,我不起眼的一言一行,竟使你抛却剔透琉璃心,着意与我诡辩起来,这是你的恨,更是你的执啊。」
我们相视而笑,他起身坐到我的身後,替我捋去白发,再将那丝白发捏在我的手掌心上,「青丝能落,戒疤可落不下,与其刻意以发遮掩,不如落尽千丝,如此一来,华发亦不必添生。」
我往额头上来回抚摸着香疤印,此时不必他以话导之,我都相信自己的决然足以抛下世俗的一切,再度归入空门。
世间多的是人想逃离,却不得也不能的,如今师弟前来召唤我,怎能不说是佛缘深厚?神京的万事万物於我而言,早已无甚可留恋之处,我人在此在彼,此心同样悠然,既是如此,宁可清闲些,悠哉些,也好过见不到师弟的脸容,反要置身这纷纷扰扰、百般烦恼的尘世泥沼中。
翌日一早,我坐上回山的马车,却发现原本要与我共行的师弟不在,仅留一笺纸,托马夫交予我,笺上梅花小楷工整,书道:
师兄:
乐以忘归的你,连我的存在也不知了,而我却牵牵挂挂、思思念念,此证你我优劣之分,师兄的豁达与随喜令我向往。
与你对话一番,我知晓自身尘心未泯,不配作为佛门子弟。我初入门时,你尝言我不适出家,此言无误矣。
不才并非避世之士,不过避人之士耳,在外既得不到解脱,便妄求逍遥无营,可惜未曾解决心病,亦对不起我佛慈悲。
深知己身执念,不愿寂寞於世,但求青史留名。此心既然动念,注定与师兄不同於途。师兄慧根高明,日後定得顿悟,成为一代高僧,传讲佛法於世。
祝修行顺利。
但恐同王粲,相对永登楼,日後愿相逢。师弟敬上
※
我回山上修行了两年,一日倾盆暴雨,天雷竟把我整间寺都轰垮了。无处可去的我只好回京寻觅妻儿,正巧寻上了,也算有缘份。妻子大骂:「这两年你都死去哪儿了,负心人!」我只字都不解释,就搬回家与他们继续生活,偶而出去找点差事做。家中妻子聪慧,儿子懂事乖巧,日子过得还算清爽。
回思近十年来所发生之事,不论我或者师弟,这禅都参不成了,想来也是种奇妙的冥助。按师弟纸条所言,他人应该还在神京,也可能在别处,总而言之,我并没兴起找他的念头。怕误了他的发展、怕打击他的信念,更怕他发现我又溜下山。我不想他知道,原来他所憧憬的师兄,不过是个比他还没用的废物。
师弟啊,你若是发达了,怎麽会需要我这个过去的累赘来羁绊你?你若不发达,又怎麽愿意被我看见穷困的一面?若我与你仍有些因缘可说,我深信自会相逢。
秋湖畔的红叶寺,是我一生中羁挂最深之处,我自儿时,至年少、成人,都在那儿度过,尽管日子稀疏平淡,却也美则美矣。最挂念的那六年在人生中所占寥寥,却也在我脑里永恒存着,一刻也挥不去,彷佛到死都会陪着我进棺材,随我的肉体一起化作尘烟。
与师弟上山采菜、与师弟秋後午睡、天冷了不免偷偷小酌取暖,这些片段彷佛能持续个十几年,只可惜我和师弟谁都选择不要这生活,如此说来,红叶寺被雷轰毁,竟也有个缘法可言。若是我佛慈悲,我愿来世与师弟作一对兄弟,互相帮衬,一块儿学习,时常都一起。
红瓦墙,青石板,京里市街繁荣,四处奼紫嫣红,百花齐放,春开牡丹,秋放金菊,在我心中却远比不上红叶寺的风光。内心驱使之下,我携一家妻小回到秋湖,并告诉他们:「你们看,这就是我出家的地方!」
妻子不听还好,一听竟扳起面孔,破口大骂:「你这不负责任的家伙居然跑来这里出家,幸好佛祖顾念我们母子俩,把你那该死的破庙劈砸了,否则你真要抛下我们不管!」
出家向来是我的人生志愿,原本我不解妻子为何不能理解我的志向,相较之下,聪明的师弟定然能理解我。可仔细想想,若雷劈红叶寺,是佛祖有意叫我不必抛家弃子,那麽与师弟的分合,必定也在冥冥之中谋合着天志吧。
我们一家人到山脚下的村里投宿时,正逢一群人来到村子里四处询问,那些人身穿家丁的服饰,其中一个向我道:「我家主人有个爱人,在这山上修行,前阵子她连人带庙遭雷劈砸了,我们主人伤心不已,希望她轮回时能再世为人,与他再续前缘,於是隐居起来,每天挨寒受冻,只服茹素,受尽苦行、折磨自身,但求速速追寻芳魂,直至今年新死了。我们为宽慰主人的亡魂,誓要将那尼姑的骨灰带回京里与主人合葬,请问你可曾听说过这尼姑的骨灰葬在哪里?」
我听得正玄之时,边上的妻子似是觉着有意思,也凑过来听,又问我:「瞧你听得津津有味,难道你认识这些人的主公?还是你知晓那尼姑是谁?」
我摇摇头,「附近只有红叶寺,这红叶寺是和尚庙,哪是尼姑庵?更何况,不论是那位尼姑,或是他们的老爷,都是死去的人,亡魂飘去哪里了也不知道,就算来找我,也不一定认得出,如此说来,又怎算得上认识呢?」
当晚,我在山村投宿,妻小与我同睡。月轮光转,繁星黯淡,夜晚的清光明明灭灭,我才睡得恍惚,朦胧间,一股山风吹入窗户,骤冷将我唤醒,而我身旁的妻小仍恍然不知,继续昏睡。世界彷佛分隔开来,醒着与睡着的两方,是为不同的阴阳两界。
我缓缓坐起身子,却见一名服紫的书生在我榻边长跪,他躬身向我合袖行礼时,腰间配戴的一组玉佩啷啷当当,声音清脆悦耳,听得我心荡神摇。我双手合十,向他颔首。
书生的模样华贵,显然已功成名就,轻启唇齿,向我道:『师兄,对不起,我的下人们不求甚解就算了,还四处乱问,竟然给你闹笑话。』
此时此刻,我特别的想抚摸他、碰触他,可不知怎地,我不敢出手,下意识的觉得不能,也摸不着,所以只能静静的看着他。
我看着他,他看着我,当下,我觉得只是说说话也足矣。我凝视着他,直过了一晌,终於道:「你若无心,家人们怎会想到那方向去?或许你口中的笑话,才是心里所谓的真话。」说的时候,我的心脏真快自喉咙口里跳出来。
那书生听完,抿着嘴唇笑了,两行清泪自眼眶里涌出,划过苍白的脸庞,点滴落在领口。
我取过帕子供他拭面,他举起长袖遮脸,在袖子後方缓缓擦拭。我避过头不去看,此时,心中方暗自酸楚起来。这是我有生以来,第一次生发这般情绪,只可惜,一切为时已晚了。
他擦拭完毕,将帕子递与我,伏地稽首道:『师兄,有劳你挂念,师弟一切无事,谢谢你。虽然说来过分,但是愿你能时常记得我,如此一来,我就完满了。』我把他自地上搀起来时,发现他的身体特别轻,彷佛轻烟一般。
「别再叫我师兄,我哪有资格当你师兄?……」我叹了一口气,察觉自己亦是满面湿润,连衣襟也沾湿一大片。「但你是我永远的师弟。」
当我醒来以後,天光既明,昨夜景象全然不复,只余襟口的泪痕依旧。